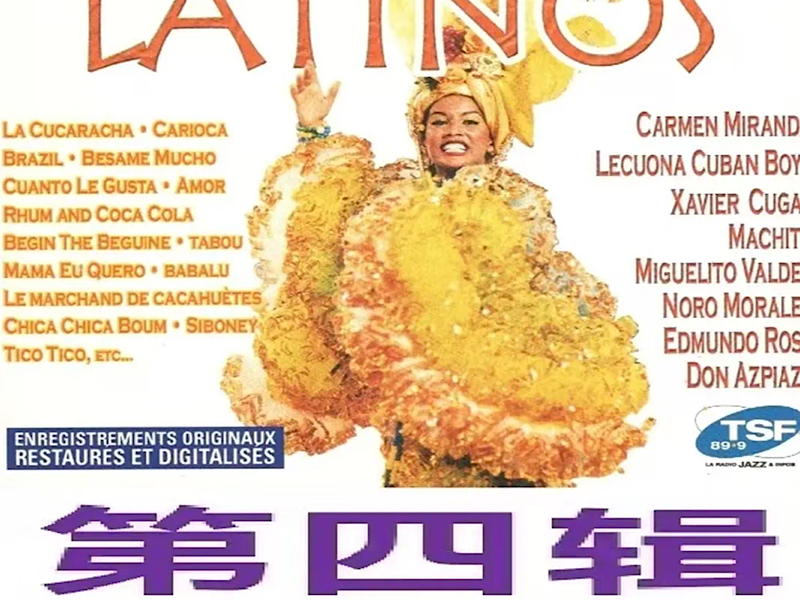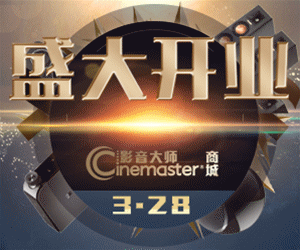每當(dāng)一個(gè)小眾東西被更多人接受時(shí),總引得很多人痛心疾首。豆瓣早就不是那個(gè)豆瓣了,果殼也不再是那個(gè)果殼,連馬蜂窩這種本來只有驢友們玩的東西,居然也出來洗腦刷屏,真是沒天理。
作家蔣方舟坦誠,當(dāng)年她知道《麥田守望者》居然是一本暢銷書的時(shí)候,自己非常失望;很多文藝青年,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么長而拗口的名字,竟然被那么多人熟知,內(nèi)心也極為崩潰。當(dāng)趙雷的《成都》火的堪比“小蘋果”和“鳳凰傳奇”時(shí),一些骨灰級(jí)民謠粉難掩自己的悲傷,尤其是趙雷又推出兩會(huì)版《成都》,更是給他們傷口上撒了一把鹽,不少人恨不得抽自己嘴巴。
即便偉大如喬幫主,當(dāng)年蘋果電腦系統(tǒng)開始跟windows兼容,使得蘋果正式進(jìn)入暢銷品行列,也傷透了大量果粉和喬粉的心,掉粉無數(shù):“蘋果你變了,你再也不是從前那個(gè)超凡脫俗的蘋果了”。這樣的例子一抓一大把,是小眾們太矯情了呢?還是大眾太俗了呢?
小眾的執(zhí)念來自自我認(rèn)同。我們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,小眾多數(shù)集中在兩個(gè)人群中,一個(gè)是年輕人,一個(gè)是文藝青年乃至中年。所以聰明的家長想要制止青春期孩子干啥事,一個(gè)高明的方式就是表示自己喜歡,孩子一看,這玩意兒,老爸老媽輩兒的這么喜歡,太LOW了,說不定就放棄了。
大眾的執(zhí)念在于想同化小眾,這是基于社會(huì)合作心理。群體中有人與眾不同是危險(xiǎn)的,“容易被野獸發(fā)現(xiàn)”、“被敵人發(fā)現(xiàn)”、“影響合作效率”,所以“痛扁那只與眾不同的猴子”是人的社會(huì)本能。但這樣的同化,反倒讓小眾產(chǎn)生守護(hù)心理,乃至產(chǎn)生“這是我獨(dú)有的私人物品”的占有感。
小眾對(duì)于大眾的抨擊和同化是不屑的,這只會(huì)增加他們快感,讓持相同意識(shí)形態(tài)的群體有更強(qiáng)共鳴。所以,小眾的執(zhí)念真的并不是“優(yōu)越感”,而是“自我”,拒絕社會(huì)化的自我。優(yōu)越感也好,占有欲也好,都是“自我”的變現(xiàn)。明白了這些,我們就能探索出打造小眾產(chǎn)品,進(jìn)行小眾營銷基本方法。
酒好還要巷子深
信息封閉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,傳播是靠口碑的,所以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。
而中心化媒體時(shí)代,傳播靠媒體,沒有聚光燈打到你身上,再好的產(chǎn)品也白搭,所以是“酒好也怕巷子深”。但圈層化和碎片化的年代,到處是發(fā)光體,到處忽明忽暗,要的是“酒好還要巷子深”。
“巷子不深”,你的酒也就看上去沒那么好了;
“巷子不深”,你的粉絲就沒有了品味壁壘,你讓他如何找到優(yōu)越感?
“巷子不深”,你的故事甚至無從講起,你就缺乏話題,單純講酒故事太自說自話了。
所謂的“深巷子”其實(shí)就是壁壘,做小眾就是做壁壘。用流行的話來說是打造鄙視鏈。
這種壁壘可以基于小眾的基礎(chǔ)(價(jià)值觀、亞文化、愛好),也可以是基于產(chǎn)品本身、渠道、價(jià)格乃至推廣方式。小米的“為發(fā)燒而生”、喬幫主的“向那些瘋狂的家伙致敬”,是基于價(jià)值觀共鳴的品味壁壘;而他們的“饑餓營銷”是制造購買壁壘,蘋果早期跟“windows不兼容”則是人為制造的使用壁壘。很多奢侈品或者一些高端場所,都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儀式感和規(guī)矩,比如雪茄要如何保存、如何點(diǎn),好的紅酒如何醒酒如何品,法式大餐有各種講究等等。這都是通過塑造壁壘來提升認(rèn)同感的方法。
十幾年前有次跟老總出差,只見他聊得興起,把手里的高級(jí)雪茄都剝成了煙絲,然后撕了張白紙條,跟農(nóng)村老大爺一樣做了個(gè)手工卷煙,抽了起來,然后直呼過癮。“這才是活出人生境界的樣子。”
國外小眾營銷成功案例很多,很多的奢侈品、潮牌、文化產(chǎn)品都是通過小眾成功,蘋果也是從小眾到大眾。歌劇作為小眾文化的代表,在西方小眾營銷做的很成功,各種儀式感,恰如其分的推廣,適度的欣賞門檻,讓歌劇成了陽春白雪的象征。而公認(rèn)藝術(shù)價(jià)值不低于歌劇的“中國京劇”,卻在國粹的幌子下,年年登上春晚舞臺(tái),逐漸淪為老年人自娛自樂的“玩意兒”。
國內(nèi)的企業(yè),大部分會(huì)把目光聚集到產(chǎn)品的物理屬性、功能屬性,成功的小眾營銷寥寥無幾。小米算一個(gè),江小白、小茗同學(xué)也正在小眾營銷的路上。其它一些本來小眾的社區(qū),如豆瓣知乎等,逐漸都走向了大眾。
小眾何去何從
可能讓很多人覺得喪氣是,大部分小眾會(huì)被大眾收編。就像大部分亞文化最后會(huì)成為或者融入主流文化一樣。當(dāng)“馬蜂窩”還叫“螞蜂窩”的時(shí)候,是小眾的,主打自由行,針對(duì)驢友們的。驢友們是好的內(nèi)容制造者,也是好的良性社群。但他們不是很好的商業(yè)變現(xiàn)者。
終于,出于商業(yè)的考慮,骨灰級(jí)驢友陳罡老板放下了小眾的架子,殺入了大眾。螞蜂窩變馬蜂窩,自由行變成了旅游指南。馬蜂窩的成功轉(zhuǎn)型為他們創(chuàng)造了巨大效益,一波世界杯的神操作后,其下載量從幾乎沒有排名,到一度超過攜程,獲得了指數(shù)級(jí)增長,以至于陳罡激動(dòng)的寫了封公開信來感謝葉總。
這是小眾人群的痛,但并不是小眾營銷的痛。“馬蜂窩已經(jīng)不是以前的螞蜂窩了”,但沒有之前不掙錢螞蜂窩哪有今天盆滿缽傾的馬蜂窩呢?
也不是所有小眾都會(huì)變成大眾,這要看這個(gè)小眾的商業(yè)變現(xiàn)力,以及企業(yè)有沒有這個(gè)能力。而且大眾和小眾還是能夠相互轉(zhuǎn)換的。毛偉人說,“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”,“不是東風(fēng)壓倒西風(fēng),就是西風(fēng)壓倒東風(fēng)。”主流和小眾是相對(duì)的。“馬克思主義”在我們這兒是主流,在有些國家卻不是。以前挺特朗普的是小眾,慢慢的變成“川黑”是小眾了。
小眾營銷的兩個(gè)基本要素是“強(qiáng)化小眾意識(shí)形態(tài)”和“制造品味壁壘”。如果你不能像鴻茅藥酒那樣一年投入100多億的廣告費(fèi),那么啟動(dòng)小眾,利用大眾和小眾的執(zhí)念,引發(fā)小眾共鳴,引起圈層化振動(dòng),最后再深度收割或者從大眾收割,應(yīng)該就是你最合適的道路。
文:農(nóng)駿